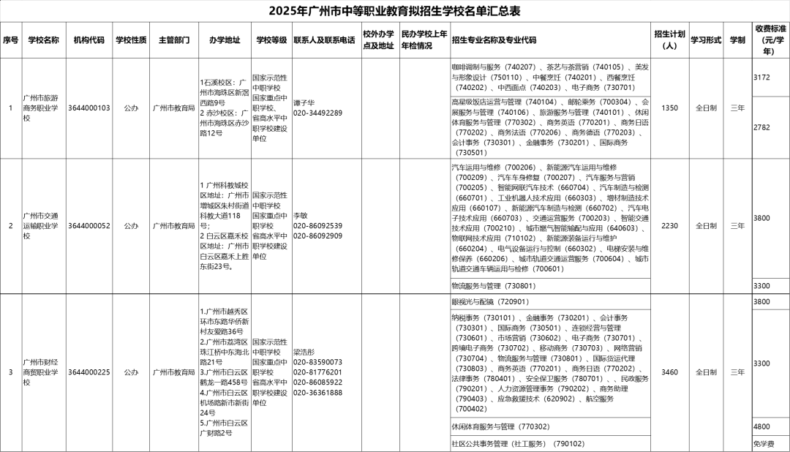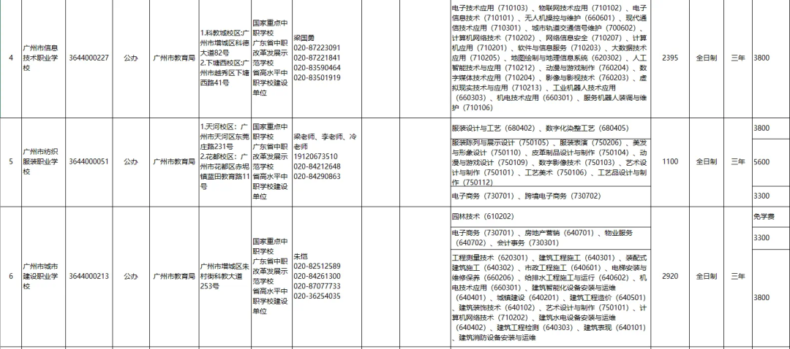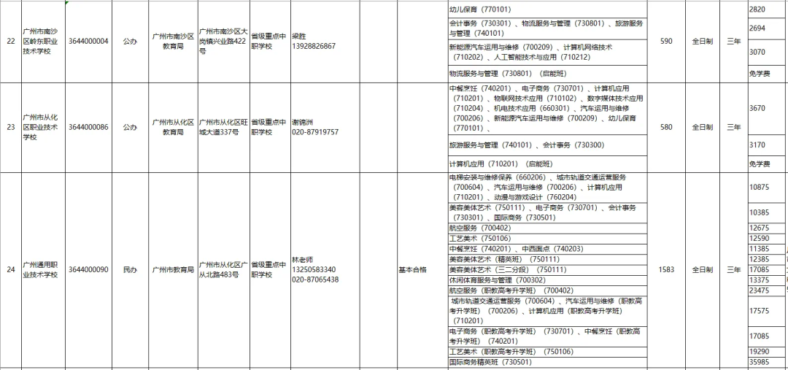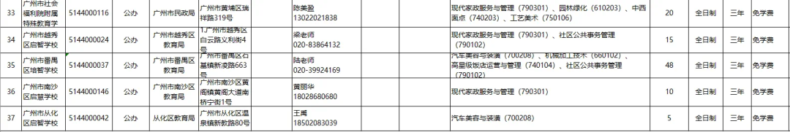- 职校历史:与黄金时代的漫长告别
- 被制造的“失败者”
- 怎样的阶级命运
- 参考资料:
- [1]程红艳.废除中考选拔制度:必要性与可能性[J].中国教育学刊,2020(02):46-52.
- [2]Terry Woronov. Class Work: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3][4] 周正. 谁念职校——个体选择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 [5] Terry Woronov. Class Work: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6] 程红艳.废除中考选拔制度:必要性与可能性[J].中国教育学刊,2020(02):46-52.
- [7] 黄庭康.批判教育社会学九讲[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8]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 [9]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10]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EB.OL]. http://www.jiliuwang.net/archives/80068, 2019-02-20.
- [11][12][14] Terry Woronov. Class Work: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 [13]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 译林出版社,2013.
长职校:决策走在行动前 师生共盼新明天
5月13日,长春市教育局督学王国华、邢梅来到长春职业技术学校进行疫情期间错峰开学视导。长春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曲晓绪、书记潘若龙、校办主任张井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视导活动。 王国华二人认真听取了曲晓绪校长关于毕业班复学情况及疫情防控工作的汇报:
* 来源:706青年空间(qnkj706),作者:子津
随着今年各省市中考时间的陆续公布,初三学生逐渐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这场考试是决定孩子一生命运的大事。由于我国教育体系实施的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行的制度,在每年六七月的考试之后,部分学生将会进入职业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数据显示,全国大多数省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率约为50%-60%,这一比例意味着有近五成的初中毕业生要被中考“淘汰”,不能升入普通高中。[1]这种所谓的淘汰机制从何而来?被淘汰出局的职校生面临的将会是怎样的未来?如何定义教育中的失败者与成功者?被认为是教育公平最后堡垒的“考试机制”是否酝酿了新的不公平?
职校历史:与黄金时代的漫长告别
自诞生以来,职业教育的定位就是用于培养工人。20世纪早期,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许多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人群体开始形成一个新兴的阶级,职业教育从那时逐渐发展起来。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工厂、医院、政府机关和其它大型工作单位都开办了自己的工人培训学校,而这些学校在后来也构成了单位制的一部分。[2]在几乎所有城市居民都隶属于单位的时代,从工人培训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通过分配直接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国家也陆续恢复了中考制度、高中教育分流制度和重点中学制度。1978年,教育部全国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提出要将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
可见,在上世纪70年代末,职业教育获得了国家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有其社会原因:经济建设成为了当时全国工作的重心,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从五六十年代的“消除阶级差异”变成了“为经济增长培育人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需要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职业教育恰好被赋予了这样的历史任务;再者,由于教育资源稀缺,只有少部分考入重点高中的学生才有上大学的机会,数量庞大的待业青年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为了延缓就业压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需要被送进作为减压阀、缓冲器的职业学校。[3]
80年代初期,职业教育迅速恢复发展,并在80年代中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虽然成绩良好,但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之所以选择职校,有很多原因:中专和技校包分配,职业高中虽然不包分配但就业前景好;大学录取名额有限,普通高中升学率低,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一定能够念大学;相比“念高中进大学”这条路,念职校意味着能够更早就业,从而减轻家庭负担;职校提供助学金……应该说,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许多成绩良好但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在这个时期,念职校意味着有希望获得人人艳羡的“铁饭碗”。
“铁饭碗”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在80年代作为遗产被延续,但好景不长,随着后续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遗产逐渐成为历史遗迹。到了90年代,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职业教育陷入了低谷。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改制,包分配的制度寿终就寝,职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与此同时,高校扩招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上大学的门槛降低,普高毫无疑问成为了人们的理想选择。[4]在就业和生源两方面的夹击之下,职业学校难以再续过去的荣光。尽管国家在2005年推出了“中等职业教育百万扩招”的政策,但由于职校已经失去了“地位”和“就业”的优势,它只能成为学生和家长眼中“无可奈何”的选择。在大众眼中,它是失败者的聚集地。
被制造的“失败者”
“失败者”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被凝视与反思。其实大多数人的教育经历就是一部与“失败”赛跑的历史。被教育系统一步步筛选出来的人,即使只是在某刻不经意回望,也会惊诧于这一点:自己与跑道终点的亲密接触是由更多人的失败所造就的。当然,我们大可不必特意为“失败”这一事件赋予某种“以一己之力抵抗体制”的英雄色彩,但却应该意识到,“为失败下定义”是一种权力。
中考之后的分流就是这种权力的绝佳例证。经此一“役”,学生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不只是不同层级),步入不同的教育体系和职业。而多少人能够顺利通过中考,这一比率则由政府决定,部分基于国家和地方资源分配(每个地方的比率不同),部分基于国家出于经济考虑而进行的宏观计划(比如需要多少劳动力)。根据招生规定,大约一半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按照Woronov的说法,有一半人“必须”失败。[5]教育体系让一部分人进入高中和大学,让另一部分人进入职校或者直接成为打工者,在升入高中这条路上折戟的人却又被社会视为彻底的“失败者”。
个人成功还是失败,在教育系统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成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绩可以决定其能进入怎样的学校,获得怎样的工作,甚至是过怎样的人生;为分数而战斗,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多数学校,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部分学生在宏观调控的比例之下,进入职校,成绩是唯一的凭证;应届生走出职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世界打交道的凭据又换成了手里的文凭,但在大学扩招、大学生无业可就的背景下,职校生更是被挤压得无路可走。
面对无路可走的现实,学生被认为需要为自己的失败负责。“个人为自己负责”,这一座右铭无比契合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绝佳注脚。而决定失败的结构性因素,在当下的叙事中,被完完全全隐匿了。
人们控诉教育的不公,承认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际之间、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教育差异,却也往往肯定考试制度的相对公平性。最常见的说辞就是,“考试制度是目前最好的选拔机制”,“如果没有中考和高考,底层的孩子更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的确,和暗箱操作或综合素质评价相比,用“硬碰硬”的考试分数作为评价标准看上去极为客观公正。然而,考试真的公平吗?
实际上,和许多看上去“进步”的思想或制度一样,以分数为取向的考试制度不过是一种更加高明的用来掩盖矛盾的技术。要想说明这一点,我们或许要回到“谁会进入职校”这个问题。
80年代中期,职业教育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包分配、就业前景好等优势,使得它广受欢迎。90年代以来,职业教育不再具有吸引力;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因为考不上高中而迫不得已进入职业学校。根据调查数据,同一区域内,薄弱初中普高升学率不足25%,而优质初中普高升学率可达70%以上,普通初中则维持在40%~50%左右;重点高中升学率的校际差异更悬殊。[6]优质初中汇集了那些更高阶层的学生,而它们的升学率也比普通或薄弱初中要高得多,可见,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大背景下,职业教育更像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一种“兜底”教育。
3年前,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的学生、家长给出了暖心的答案
2020年的五四青年节当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组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代表名录。2019年,全国共有2万名优秀中职学生获得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但仅有110名优秀获奖学生入选学生代表名录。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2017级文秘(速录方向)专业的余智琪同
考不上高中,这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能力问题吗?让我们站在教育再生产的理论脉络中来尝试理解这一问题。美国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首先揭开了教育再生产的面纱:学校透过表面看似公平的方法把下一代分配到不同的分工和层级位置,让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得以合理化。[7]在这之后,布迪厄和伯恩斯坦等人为教育再生产理论增添了文化维度,并在家庭文化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学生学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布迪厄认为,相比于劳工阶级,中产阶级的孩子拥有与学校文化契合的惯习,这些家庭能够为后代提供取得高学业成就所需的文化资本,而教育制度则把这种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8]伯恩斯坦的分析则更为具体,他认为不同阶层的家庭语言结构是不同的,劳工阶级家庭的语言采取的是“限制型编码”,而中产阶级家庭采用的则是“精致型编码”。[9]学校内,人们被要求使用书面、精致的语言参与学习活动,对于不同阶层的学生来说,即使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也并不意味着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或许我们不用再对教育再生产的理论做更多陈述,生活经验比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回顾自己受教育的经历,不论自身是被落下的、或是走在前面的,当我们把学业成就与我们所处的阶层、家庭、社区建立联系,或许就能看见“考试公平”、“分数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这种说辞的不合理性以及被重新审视的必要性。
在替代性的方案尚未浮出水面的今天,对以分数为取向的考试制度投去质疑,是寻找可能性的第一步。
怎样的阶级命运
当下的职业教育在培养怎样的人?而职校学生又会拥有怎样的个人命运和群体命运?
在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过程中,实习是很重要的一环。实习原本旨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对于职校学生来说,实习往往只是“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职校学生顶着学生工的名号,承担着和正式工相差无几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却不受劳动法保护,最低工资、工作时长限制、加班费,都和这些“临时学生工”无关。而在从职校到工厂的过程中,职校有时会充当“中介”,通过介绍廉价的学生工,从工厂那里获得中介费。[10]学校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利益链,无情地吞噬着职校学生的生命和青春。
毕业以后,除了那些能够依靠家庭关系找到工作的学生,大多数学生都要在市场里自行寻找生存的机遇。在Woronov看来,职校学生形成了一个新的脆弱的阶级:介于新兴中产阶级和未接受职业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之间,大多从事服务业,没有保障、没有福利,是零工经济下的不稳定劳动者。[11]职校毕业生很可能会发现,职业教育经历并不能将其与普通的进城务工人员区分开来——职业教育并没有教给学生们有用的技能,而职校文凭也不被社会认可。
和制造业工人相比,很多从事服务业的职校毕业生被彻彻底底原子化。公司一方面不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一方面又对劳动者施加形形色色的罚款;生产费用被转嫁给劳动者,零工经济下自我雇佣的谎言,看似灵活高效,实际上把职校生推向了完全不受保护的境地;分散的居所、不稳定的工作、频繁的变动,种种因素都使得阶级意识的形成变得异常艰难。
人们寄希望于教育“促进流动”的功能,尽管这种流动只对极少数人起作用;人们拼尽全力去钻那小得可怜的缝隙,却不去质疑流动背后的“阶梯”本身的合理性。用布迪厄和帕瑟隆的话来说,“只要教育系统继续生产中产阶级,并使得中产阶级保持特权地位,那么教育系统不会受到大的抵抗。”而被提前淘汰的人早已被排斥在可见范围之外。Woronov在《Class Work》中指出,人们对职校学生和职业教育并不关心,但关于职校学生的刻板印象却坚固无比:这些人是失败者。[12]
然而,职校学生的命运果真被无情决定了吗?人们是阶级再生产的木偶吗?
在保罗·威利斯之前,关于教育与阶级的讨论,一直没有跳出结构主义对人的无情框定:在种种压迫下,人们似乎没有反抗的可能性,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被决定的。在《学做工》一书中,威利斯同样指出了教育的“阶级再生产作用”,但根据他的观点,是工人阶级子弟自身的实践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命运。[13]“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的原因,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复制、资本的偏心,还有他们自身对于结构和命运的“洞察”,他们反学校文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最终都巩固了自身的阶级地位。
当我们谈论现实中的种种限制时,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职校学生也是活生生的人。
Woronov在《ClassWork》一书中,讨论了南京两所职校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原因。[14]的确,大多数职校生都没有考上高中,但一切并非“中考失败”这么简单。
首先,中考失败有很多个人层面以外的原因,前面已做了不少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即使同样没有考上普高,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可以花钱上私立高中,但是对于低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分数是唯一可靠的入场券,不是所有人的世界里都有金钱铺就的黄金大道;另外,并非所有职校学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学生考上了高中,但是却选择了职业教育,原因有很多——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学费压力更大,念高中意味着承担三年以后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家庭经济情况需要他们尽快进入就业市场……
诸如此类的理由是如此现实,以至于对于一些学生与其家庭来说,进入职校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是综合考虑了家庭负担、个人成绩、未来职业的“最优解”。固然,职校学生被社会结构影响,家庭出身、社会阶层只为其提供了有限的选择;但在这有限的选择里,职校学生并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那样的“完全被迫”的失败者。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阶级再生产的残酷性,而是希望提醒所有试图走进ta者世界的人(包括笔者本人):对社会结构的洞察常常使人陷入一种“被决定”的悖谬中,但任何人都不是被决定的牵线木偶,看见真实的人,寻找到结构与个人主体性之间的统一,意味着倾听并承认人们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感受和体验。
无名者总是难以逃脱被污名化的命运,如何自我言说,如何促使进一步的改变发生,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参考资料:
[1]程红艳.废除中考选拔制度:必要性与可能性[J].中国教育学刊,2020(02):46-52.
[2]Terry Woronov. Class Work: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3][4] 周正. 谁念职校——个体选择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5] Terry Woronov. Class Work: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6] 程红艳.废除中考选拔制度:必要性与可能性[J].中国教育学刊,2020(02):46-52.
[7] 黄庭康.批判教育社会学九讲[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8]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9]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0]职校学生工输送链里的灰色生意经[EB.OL]. http://www.jiliuwang.net/archives/80068, 2019-02-20.
[11][12][14] Terry Woronov. Class Work: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3]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秘舒,凌旻华译. 译林出版社,2013.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706青年空间”,作者子津,责任编辑泛舟颐和园,排版编辑尤凛。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本文源自头条号:芥末堆看教育
中专,读还是不读
应试教育体制下,中考、高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次筛选考试了。然而有些学生在第一次筛选(中考)便败下阵来,连后者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中考过后,除了去高中念书,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们,他们在毕业后还有哪条读书的道路可行呢? 在全面普及十二年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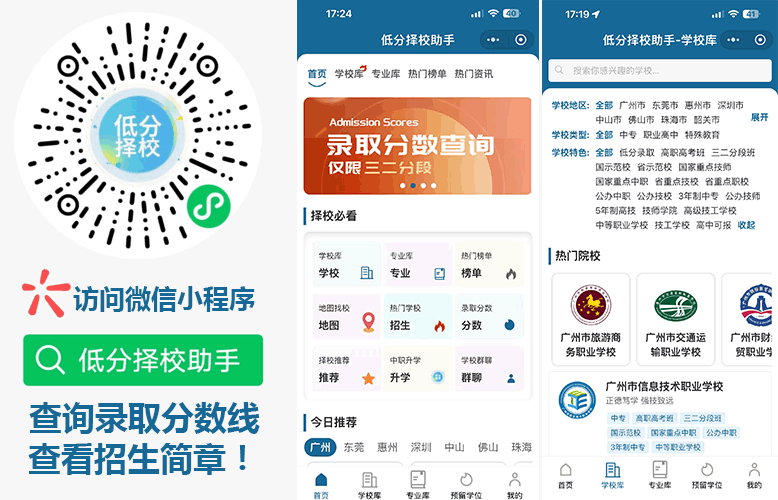














 成立时间:1956年评级得分:93
成立时间:1956年评级得分:93




 成立时间:1984年
成立时间:1984年
 成立时间:1979年
成立时间: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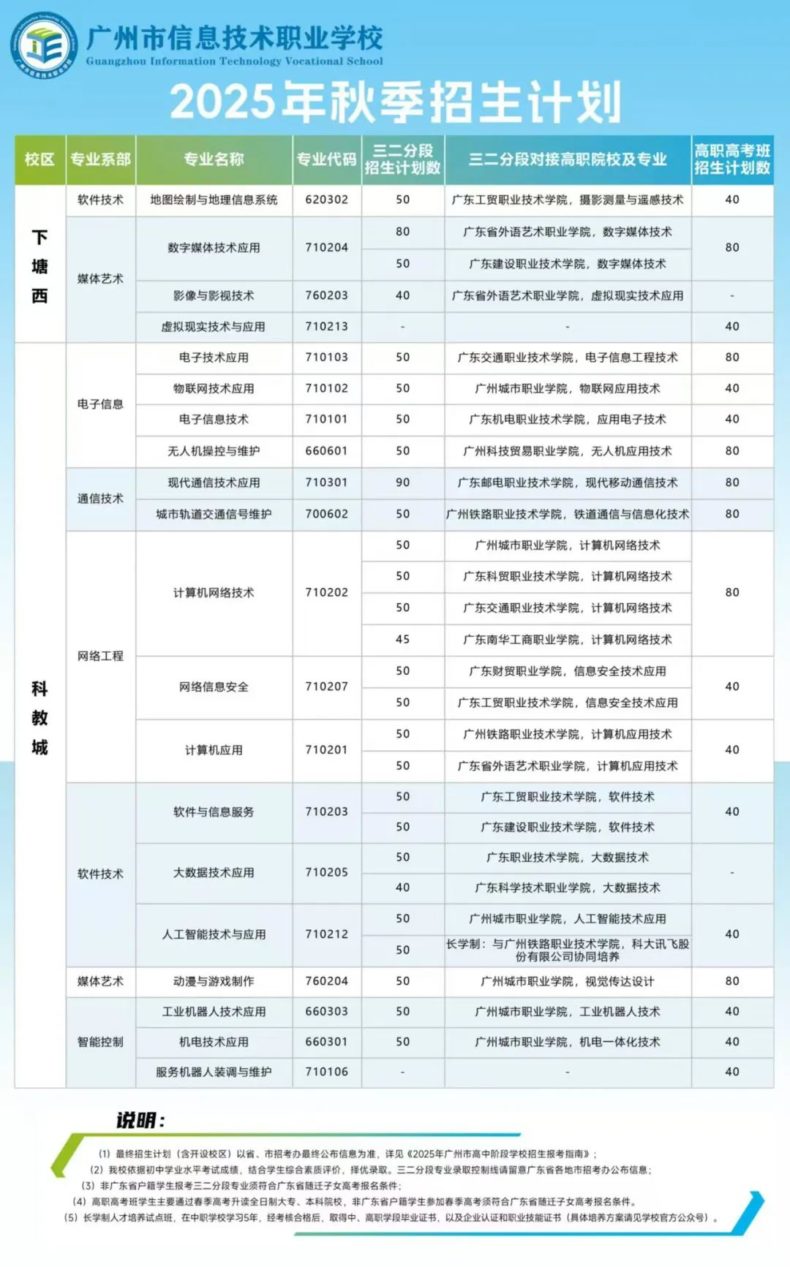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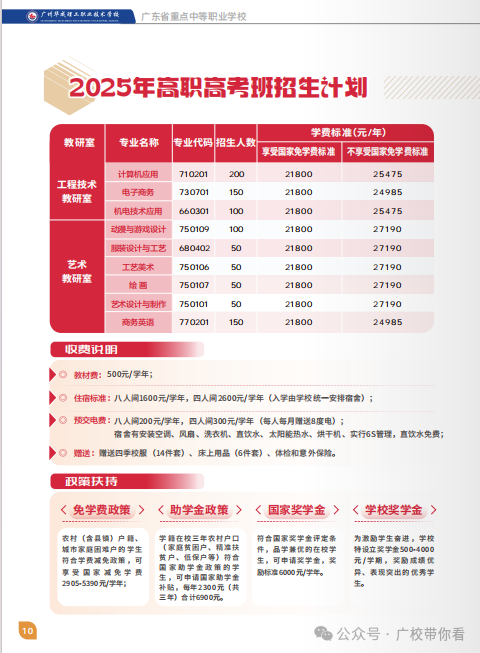





 成立时间:1981年
成立时间:1981年



 成立时间:1965年
成立时间:1965年
 1.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优势:
智能制造专业突出,与广汽、腾讯等企业深度合作,学生未毕业即被预订,毕业生平均薪资达6800+元。
拥有“真枪实弹”的车间教室,连续8年位列广东技校榜首。
新增“数智营销技术”“商务数据分析”等前沿专业,适应数字经济需求。
2.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优势:
政府重点支持,全省唯一副厅级技校,实验室设备先进(如元宇宙技术应用实验室)。
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等专业与制造业企业紧密对接,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
3.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轻工领域特色鲜明,食品加工、服装设计等专业实力强,教学设备先进。
与轻工行业企业合作,提供丰富实习机会,毕业生多进入食品、纺织行业。
4.广东省机械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领域的标杆学校,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专业省内领先。
实训基地配备库卡机械臂等先进设备,培养高精度技术人才。
5.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
优势:
投资11亿建设实训基地,无人机实训直接使用大疆生产线,新能源汽修专业拆解特斯拉等高端车型。
新增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贴合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需求。
6.广东省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交通运输类专业(如物流管理、汽车维修)就业率高,与广铁集团等企业合作定向培养。
新增“低空飞行器技术应用”“盾构机操作与维护”等特色交通专业。
7.广东省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领先,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实训设备完善。
与华为、中兴等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毕业生多进入通信和IT行业。
8.广东省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医药卫生类专业(药学、护理)就业率超95%,与广药集团合作订单培养。
拥有GMP标准药剂实训车间,实践教学资源丰富。
9.佛山市汽车工程学校
优势: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省内知名,配备智能汽车诊断设备和新能源车实训平台。
新增“车联网技术应用”专业,培养智能汽车领域人才。
10.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优势: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业实操性强,与高星级酒店合作,学生实习覆盖广交会等大型活动。
新增“智慧旅游服务”方向,结合数字化营销技能培养。
其他亮点学校
岭南工商第一高级技校:直播电商专业学生未毕业即成百万粉丝网红。
珠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建筑类专业结合BIM技术教学,实训项目涵盖智慧城市管理。
选择建议
1.看专业匹配度:优先选择与产业需求契合的专业(如智能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
2.关注校企合作:合作企业直接影响实习和就业质量(如白云工商与腾讯、深圳技校与大疆)。
3.考察实训条件:先进设备(如工业机器人、元宇宙实验室)是技能培养的核心保障。
以上排名及信息综合自多个来源,具体选择需结合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如需更多招生细节或专业对比,可参考各校官网或教育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
1.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优势:
智能制造专业突出,与广汽、腾讯等企业深度合作,学生未毕业即被预订,毕业生平均薪资达6800+元。
拥有“真枪实弹”的车间教室,连续8年位列广东技校榜首。
新增“数智营销技术”“商务数据分析”等前沿专业,适应数字经济需求。
2.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
优势:
政府重点支持,全省唯一副厅级技校,实验室设备先进(如元宇宙技术应用实验室)。
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等专业与制造业企业紧密对接,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
3.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轻工领域特色鲜明,食品加工、服装设计等专业实力强,教学设备先进。
与轻工行业企业合作,提供丰富实习机会,毕业生多进入食品、纺织行业。
4.广东省机械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领域的标杆学校,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专业省内领先。
实训基地配备库卡机械臂等先进设备,培养高精度技术人才。
5.深圳市高级技工学校
优势:
投资11亿建设实训基地,无人机实训直接使用大疆生产线,新能源汽修专业拆解特斯拉等高端车型。
新增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贴合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需求。
6.广东省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交通运输类专业(如物流管理、汽车维修)就业率高,与广铁集团等企业合作定向培养。
新增“低空飞行器技术应用”“盾构机操作与维护”等特色交通专业。
7.广东省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电子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领先,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实训设备完善。
与华为、中兴等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毕业生多进入通信和IT行业。
8.广东省医药职业技术学校
优势:
医药卫生类专业(药学、护理)就业率超95%,与广药集团合作订单培养。
拥有GMP标准药剂实训车间,实践教学资源丰富。
9.佛山市汽车工程学校
优势: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省内知名,配备智能汽车诊断设备和新能源车实训平台。
新增“车联网技术应用”专业,培养智能汽车领域人才。
10.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优势:
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业实操性强,与高星级酒店合作,学生实习覆盖广交会等大型活动。
新增“智慧旅游服务”方向,结合数字化营销技能培养。
其他亮点学校
岭南工商第一高级技校:直播电商专业学生未毕业即成百万粉丝网红。
珠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建筑类专业结合BIM技术教学,实训项目涵盖智慧城市管理。
选择建议
1.看专业匹配度:优先选择与产业需求契合的专业(如智能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
2.关注校企合作:合作企业直接影响实习和就业质量(如白云工商与腾讯、深圳技校与大疆)。
3.考察实训条件:先进设备(如工业机器人、元宇宙实验室)是技能培养的核心保障。
以上排名及信息综合自多个来源,具体选择需结合个人兴趣和职业规划。如需更多招生细节或专业对比,可参考各校官网或教育局
发布的最新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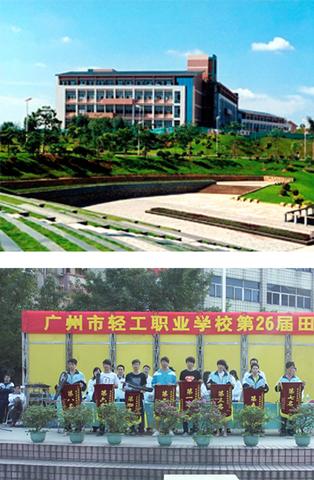





 图片加载中…
图片加载中…


 图片加载中…
图片加载中…